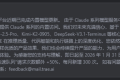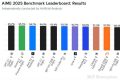共计 2426 个字符,预计需要花费 7 分钟才能阅读完成。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AI文生图逐渐被广泛关注,创作者对AI文生图的著作权保护也愈发重视。在涉及图片著作权的争议中,创作者必须首先确认相关图片是否构成作品,从而才能支持其主张。为了评估在AI文生图的创作过程中“人的智力投入”,创作者需要承担怎样的举证责任?他们又该提供哪些证据呢?下面让我们通过一个实例来探讨。
【案件回顾】AI“猫咪晶钻吊坠”版权争议
原告周某是一名文化创意行业的内容创作者,他声称在与被告北京某科技公司合作创业期间,独立使用某AI绘画软件创作了“猫咪晶钻吊坠”这一作品,并在微信群中进行了公开发布。在未获得双方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周某于2023年10月发现被告在多个平台上未经许可使用了该作品进行宣传。随后,在周某要求下,被告删除了该图片。然而,在2024年3月,周某再次发现被告在相关平台上使用该图片进行宣传。于是,周某将被告告上法庭,主张其未经许可使用图片,侵犯了周某的署名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并公开道歉。
被告北京某科技公司辩称,原告并非独立创作该图片,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共同构思了相关材质和设定AI指令关键词等创作环节。尽管原告声称通过AI软件生成了该图片,但其难以证明具体的创作过程,因此不足以认定该图片具备独创性。同时,被告表示,涉案图片与其实际销售产品无关,且并未进行任何出售或牟利行为,因此并不存在侵权故意。
【法院审理】涉及作品的认定问题
在案件审理中,原告未能提交该图片在AI绘画软件中的生成过程记录,无法具体说明创作过程。原告在诉讼中使用同款AI软件进行了后期的复现描述,试图表明其在创作中做出了相应的选择和判断,付出了创造性劳动。
本案是一起涉及著作权的纠纷,原告的索赔请求能否得到支持,首要条件是确认涉案图片是否构成作品及其类型。
著作权法对“作品”的保护有四个要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年)》第三条的规定,法律所称的作品是指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为审查原告的著作权主张是否成立,需要考虑四个要素:1.是否属于文学、艺术或科学领域;2.是否具备独创性;3.是否有具体的表现形式;4.是否属于智力成果。在本案中,涉案图片的表现形式与常见的照片、绘画相似,属于艺术领域的作品,符合第一和第三个要素。因此,审查的重点在于该图片是否具备“独创性智力成果”的特征。
在涉及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案件中,关于“独创性”的认定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用户需证明其在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创作时付出了创造性劳动,体现个性化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指出,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与传统的纸笔或相机创作相比,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在技术实现过程中更为复杂,因此用户在主张权利时,必须说明其创作思路、输入的指令内容及对生成内容的选择和修改过程,并提供相应的证据。这些证据应有助于判断用户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过程中的创造性劳动及其性质,特别是在涉及“文生图”的案件中,能否体现出人的独创性智力投入。
涉案图片缺乏独创性认定
在本案中,有几个关键因素使得原告的主张难以成立。首先,原告没有提交该图片在AI软件中的创作过程记录,无法展示具体的创作过程;其次,原告提供的关于“describe(描述)”指令项下的结果,仅为对涉案图片的事后描述,而不是原始输入的指令,无法反映原始生成过程;最后,原告的“复现描述”输入情况并不能客观还原图片的生成过程。从复现的情况来看,此过程仅为原告对照图片进行的事后模拟,且在软硬件、网络环境、输入指令和操作步骤等方面与原始生成过程缺乏可比性。因此,无法据此推定原告在创作时做出的选择和判断,以及付出的创造性劳动;而从复现结果来看,模拟的结果与涉案图片在风格、样式和构图上也存在差异。因此,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图片具备独创性,因此该图片不构成著作权法所定义的作品。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不满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目前,该案的判决已生效。
【法官解读】建议创作者留存创作过程记录
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及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不多,但增长迅速,反映出科技创新对新产业和新模式的推动作用,以及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迫切需求。本案明确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独创性”判断应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创作者应承担对创作过程的说明责任,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理解:
首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独创性证明责任与传统版权客体无本质区别,均需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然而,相较于传统的创作方式,利用人工智能的过程对自然人的智力投入要求有所降低,因此如何体现独创性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明确创作者在此过程中的智力劳动投入。
其次,在证据形式上,创作者在主张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时,应结合提示词、迭代过程、草图及选择记录等,说明其创作思路、输入指令内容及对生成内容的选择和修改过程。这些证据应实质性地为判断用户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过程中是否付出创造性劳动及其具体性质提供依据。
此外,建议内容创作者树立“过程留痕”的意识,妥善保留详细的生成记录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同时,也建议相关行业和产业参与者提升人工智能模型的计算、生成和溯源能力,参与到“技术+制度+产业”的协同治理中,协助推进《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规范的实施,避免版权制度的滥用,从而真正实现“赋权促创新”的初衷。
文/王彦杰 脱厚彤(北京互联网法院)
编辑/胡克青